2020年11月,美国某著名大学的一位院长级别教授在一个新闻采访上说,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的粉丝们对这一团体的狂热追逐类似宗教崇拜。一个星期内,这位教授收到将近300封来自防弹粉丝的邮件,对其进行近乎人身攻击式的批评,言语中充满了指责与不屑。后一年的9月,当我对有关K-pop的学术讨论进行了一年多的阅读,自认为对K-pop在美国流行的现象有了一定的认识与反思时,我给该教授写了一封长邮件。在邮件里,我强调这位教授的遭遇代表了两种价值观的对撞:美国精英大学与K-pop产业。我写道,美国精英大学远非单纯教学科研机构,而是一套抽象的价值体系;同样,K-pop远非音乐与舞蹈,而是一套更抽象的价值体系。而美国私立大学与欧洲大多数大学的区别类似于K-pop与欧美流行音乐区别的关系,前者以后者为基础,但又发展出后者不具备的一套俘获全世界人心的光环效应与眩晕感。因此,当那些K-pop粉丝并没有因为该教授的名头而吓到,反而以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姿态对其进行批评时,本质上说明作为美国最成功的奢侈品的精英私立大学,在另一种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奢侈品K-pop面前失去了光环,后者比前者拥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这位教授不愉快的经历背后,本质是美国精英大学叙事及其文化领导权的一次重要失败,美国群众可以通过K-pop去想象另外一套价值体系与认同感,而防弹少年团则是这一套另类叙事的代表性符号。
邮件发出数天之后,我收到了这位教授的回复,她完全没有被我的一些看似不同寻常的想法所冒犯,相反,她透着激动说,我像是一位真正的战友说出了问题的根本所在。可以想象,当这位教授所在的精英学府的同事们了解到其遭遇时,很有可能都是用不屑的态度说,不要去和追星群众计较。而我却将其遭遇上升到了美国精英大学及其挑战者的碰撞的维度。我之所以选择用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这位教授的经历,是因为我确信,她愿意出来评论以防弹少年团为代表的K-pop现象,是从学者的角度给予了K-pop现象足够多的重视与尊重。而我认为,批判性是学者的本性,其认为对防弹的狂热是一种宗教崇拜的观点可以进一步讨论和商榷,但她无疑是在履行作为学者的本质性职责。
这位教授的遭遇是防弹少年团粉丝组织“阿米”(ARMY)在美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一部分。我认为K-pop在美国由亚文化走向主流有三个标志性事件:一是防弹粉丝干预特朗普选举;二是防弹粉丝支持黑命贵运动;三是拜登接见防弹成员讨论亚裔仇恨问题。特别是,防弹在2019年的自传性歌曲《狄奥尼索斯》中通过对公元前5世纪末古希腊悲剧《酒神的伴侣》里部分剧本内容进行改编,将防弹成员与粉丝的关系暗喻为古希腊民众在酒神节音乐舞蹈下狂欢的状态。而那位著名学府的教授与防弹粉丝之间的不愉快的经历,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酒神的伴侣》里作为酒神文化反面的彭透斯(Pentheus)。

防弹少年团《狄奥尼索斯》现场舞台表演
正是基于这次经历,2022年7月,我在给国内高中生开的暑期线上课“理解流行文化”的最后一次课程里,再次强调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以防弹少年团为代表的K-pop的狂热不是简单追星,而是青年人社会运动及其诉求在社交媒体时代的集体表达。与此同时, 在比较1960年代披头士狂热与现在的防弹热时,我以极其肯定的口吻说,如果我们把流行文化潮流作为群众心理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来看待的话,从解释过去的角度看,披头士热预示了1968年欧美学生运动的到来;而从预测未来的视野来说,现在欧美对防弹的狂热则预示着1968的再现。一年半之后,随着巴以冲突引发的美国校园大规模示威,这一预言成为了现实。这也让我进一步坚信,把K-pop作为观察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一种视野是可行的。如果说剧作家理查德·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的剧作《六九年的狄奥尼索斯》(Dionysus in 69)体现的是那个年代的时代精神,防弹五十年后的歌曲《狄奥尼索斯》就像在为那个时代招魂,而这个狄奥尼索斯的幽灵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将酒神召唤了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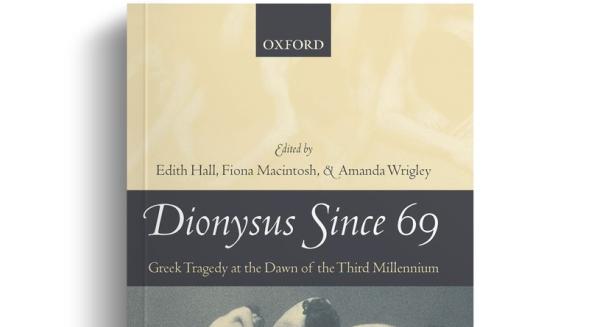
英国三位著名古典学家主编的《自69年的狄奥尼索斯:在第三个千年前夕的古希腊悲剧》(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对狄奥尼索斯在当代西方的接受进行了考察。熟悉狄奥尼索斯符号的古典学家都不会否认防弹2019年的《狄奥尼索斯》在这一谱系上。
今年8月中旬,由来自美国人文社科不同领域的六名学者(都是少数族裔女性)主编的包含有28篇文章与15件画作的《防弹再混合:防弹少年团批判性读本》(Bangtan Remixed: A Critical BTS Reader)(以下简称《读本》)由杜克大学出版。该书前言同样传达了类似观点:“《防弹再混合》讨论的是防弹少年团让什么事情变得可能与可被察觉,其运用防弹少年团作为一个视角去研究历史、美学、经济、文化、社会性与地缘政治。”(《读本》第4页)在今年3月,我收到杜克大学出版社编辑的邮件,让我考虑就这本书写点东西。一开始,我设想的是,我要写的是一篇正常的学术书评。但是,当我第一次把这本书通读一遍后,我感到这本书无法用一般写学术书评的方法来评论,因为这本书里面文章的作者背景、风格和内容差异之大已经远远超出一部学术论文集的范畴。换句话说,这本书更像是一部带有学术色彩的由防弹粉丝们集体创作的文艺作品。

《防弹再混合》,杜克大学出版社
如果用学术标准衡量,《读本》中可能不少文章都会被认为是带有明显学生习作痕迹或需要大改的文章初稿。该书六位主编都在各自领域里有所建树,不少都有学术专著并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对传统学术标准的了解无疑比我更透彻。我认为,六位编者的征文与编辑的目的不是让该《读本》只呈现传统学术写作里的研究型论文,而是要呈现多种声音,有些甚至超越了学术写作本身(其中一篇是完全的自传性日记)。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应该将《读本》作为一件文艺作品去进行批判性阅读,就像我之前反思那位教授的遭遇那样,用《读本》去反思背后学术文化政治的变迁。

《读本》六位主编,图片来源:《防弹再混合》INSTGRAM官方账号
就这本书写书评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为什么美国那么多人文社科学者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K-pop粉丝?在三年前,我对耶鲁大学社会学家高玉蘋进行采访时,她直言不讳地说,是她作为亚裔美国人感受到的边缘性地位,让她在疫情期间成为K-pop粉丝。这绝非个例。《读本》作者之一、斯坦福大学艺术史学者马西·权(Marci Kwon)在2022年斯坦福大学召开的一场关于K-pop的会上,曾非常生动地说:
我认识的所有亚洲女性教授在疫情期间都入坑了K-pop……有色人种女性对K-pop的兴趣对我来说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当我看到K-pop在美国的成功时,不禁感到一丝满意,这些亚洲男性和女性在美国这个仍然认为亚洲各种语言和人群都一样且外来的国家里,正在以我们(美国自己)的方式击败美国。看到韩国文化的迅速崛起及其动摇美国自我特殊性的方式,令人感到愉悦。
这一说法可能略带夸张(至少我可以列举出好几位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有亚洲背景的女性教授并没有成为K-pop粉丝),但和高玉蘋的自述结合起来看,的确体现出某种普遍性。而我认为,《读本》的一大价值,就是为反思这个现象提供了一个“文本”。如果我们把《读本》看作进入K-pop的学者们的一次集体表达而非一部冷静客观的学术著作,就可以把该书作为对相关现象进行元学术性反思的一个重要症候文本。如果说我与那位著名教授就K-pop作为美国私立精英大学外的另类价值体系达成了共识,《读本》又如何帮助我们反思这一现象?
我认为,著名学者汪晖在其代表性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以下简称《兴起》,去年部分翻译为英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今年韩国出了韩文全译本)中为反思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维度。在这本书里,汪晖通过勾勒中国在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儒家天理世界观向科学公理世界观的转变(现代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兴起则作为这一转变的制度化表现)及其与资本主义和技术文明的交织,进而从中国“边缘“对欧美“中心”进行现代性批判。特别是通过下卷第二部《科学话语共同体》里对张君劢从人文角度反思科学的具体分析,汪晖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从人文主义角度对公理世界观下社会科学的批判及现代学科划分及教育的反思,展示了现代公理世界观与科学话语共同体内部的内在张力。而我认为以防弹代表的K-pop在美国的流行及其在美国学术界表现的文化症候——无论是那位著名教授的遭遇还是《读本》的出版——都表明我们现状可能处于另一个历史节点上:社交媒体时代的科学公理世界观及相应的科学话语共同体面临着大众文化的挑战并正在开始转型。可以说,汪晖此书为理解当下流行文化提供了一种视野,我们可以通过《读本》去思考,一群在科学公理世界观和科学话语共同体训练下成长的学者,如何开始通过学院之外的大众传媒文化寻求一种后公理世界观以及对科学话语共同体的超越,即对公理世界观及科学话语共同体的批判已经不再是一种内部文人知识分子脱离社会经济文化实际的形而上玄学清谈,而是开始借助传统知识分子与学界的对立面——当代媒体塑造的大众文化——去重新思考学者与社会的关系。当我们从传统学术角度说《读本》里不少文章都有待提高时,或许可以换一种视角,将六位熟知当代学术话语与规范的主编主动抛弃传统学界评价标准、尽可能地在《读本》里融入各种声音和吸纳非学术表达方式的做法,看作是在流行文化驱使下超越传统科学话语共同体狭隘性的一次尝试。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多种语言译本,图片来源,“清华文科”官方微信号
在下文中,我将以这个视角去重新思考《读本》里文章的意义。但在此之前,《读本》里有两篇文章需要单独介绍。在我看来,这两篇文章的意义有二。首先,其批评性与论证的透彻性是《读本》里最符合传统学术研究期待的。其次,这两篇文章也为进一步思考以防弹为代表的的K-pop现象及《读本》本身从学理上提供了重要视角。
第一篇是该书的第14章,由主编之一、研究菲律宾与夏威夷的人类学家韦尔纳黛特·维库尼亚·冈萨雷斯(Vernadette Vicuña Gonzalez)撰写的《帝国进行中:跨太平洋流动的护理工作》(Empire Goes On: Transpacific Circuits of Care Work)。在该文里,作者以2016年在夏威夷拍摄的一档综艺节目《Bon Voyage》里防弹成员观看夏威夷土著草裙舞发出赞叹的特写镜头为切入点,反思美国帝国主义在太平洋的表现及其触发的服务经济。作者强调,夏威夷舞蹈为反思K-pop和K-pop偶像是什么提供了一个棱镜,与夏威夷舞者一样,K-pop产业源自美国在太平洋帝国主义的服务经济。作者进而对拜登因针对亚特兰大亚洲按摩师的枪杀事件而接见防弹成员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作者强调,一方面,美国反亚裔情绪本身就植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自身结构,这一结构包括美国驻韩军营催生出的服务性经济,而在枪杀里遇难的六名亚洲女性按摩师(四名是韩国人)则根源于这一帝国军事经济结构;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拜登选择美国帝国主义下的服务型经济的另一部分——K-pop产业及偶像——来为亚裔仇恨发声,只能是一种政治与娱乐结合的作秀(showmanship)。有人认为拜登找韩国人讨论美国内部问题违和,作者指出,七位防弹成员进入了白宫不是去到了外国,他们是从美利坚帝国边缘(韩国)回到了帝国中心(华盛顿特区)。而疫情期间美国大量民众从防弹的歌曲与在线表演里找到慰藉,本质上是防弹在履行他们作为美利坚帝国下的亚洲服务人员为帝国中心的美利坚民众们提供情感上的服务劳动,而这一服务劳动带有强烈的种族与性别标志性。因此,作者的中心论点是:拜登召见防弹是基于美国帝国服务经济,动员他们为美国服务的一次符号性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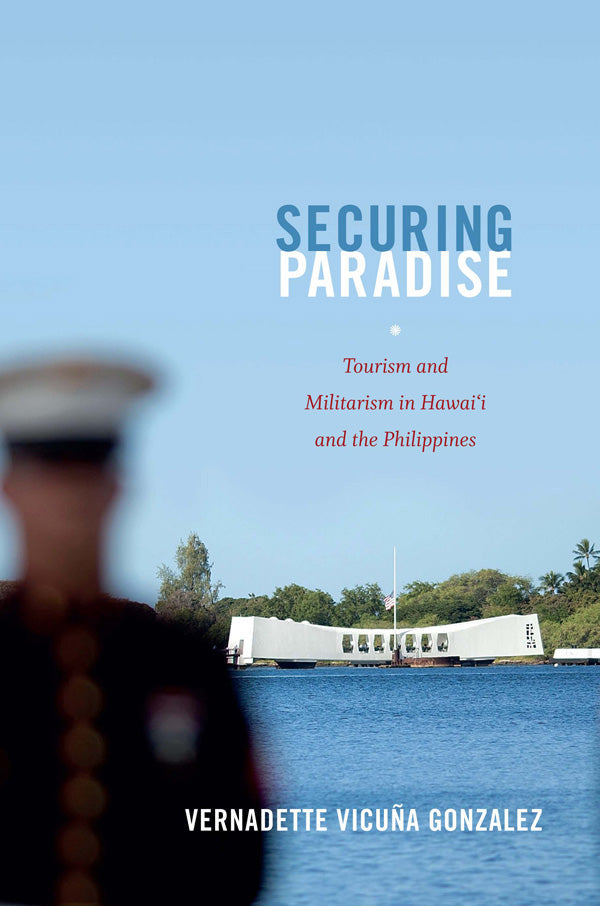
韦尔纳黛特·维库尼亚·冈萨雷斯研究夏威夷与菲律宾的专著《天堂安保:夏威夷与菲律宾的旅游业与军事主义》,杜克大学出版社
媒体与电影学者Rachel Kuo在《像卧底罪犯:爱、恨与包容性的展演》(Like a Criminal Undercover: Love, Hat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Inclusion)对拜登接见防弹成员进行了具有同等批判性但带有不同角度的解读。同样是在韩国作为美利坚帝国的一部分的前提下(作者用美国“占领”韩国一词来强调这一帝国结构),作者指出美国官方和主流话语下的反亚裔仇恨带有自相矛盾之处,作者认为亚裔仇恨并不是个体行为,而是美国帝国主义内部结构的本质的一部分,而反亚裔仇恨话题则是美国官方与主流试图用“仇恨”这样带有高度主观性与个体性的话语,将美国帝国主义的结构性问题归咎为一群人的个人问题。在这样的视角下,作者将拜登接见防弹看作是通过这一“仇恨”话语逃避责任的戏剧性表演。像一般K-pop学者分析音乐视频一样,作者将展现防弹成员进入白宫并与拜登交流的视频看作是一段高度表演化的视频,并将这一事件与美国历史上“解决”亚裔问题的政治行为相联系(比如里根在1988年谴责由于美日经济竞争导致的底特律仇杀华人问题)。作者跳出了K-pop本身,把拜登接见防弹成员这一事件纳入到美国种族关系历史中加以考察。作者特别指出,防弹成员在2022年12月面临兵役,本身就再次提醒大家美国对韩国进行军事占领这一事实,而反亚裔本身就是美国在亚太的帝国主义部署导致的结构性问题。

拜登接见防弹成员
从传统学术标准出发,这两篇文章无疑代表着K-pop研究甚至文化研究的理想范本,问题意识明确,批判性极强,能跳出K-pop看K-pop,对所分析的视频能直达重点。特别是,维库尼亚·冈萨雷斯是以研究夏威夷和菲律宾问题见长的人类学学家,她把研究夏威夷和菲律宾与美国在太平洋的帝国主义的视野,转移到太平洋西岸的朝鲜半岛上,贡献了传统中日韩东亚视野下看待韩国完全不具备的角度。论文的第一部分对防弹几个音乐视频的分析,《IDOL》里的传统朝鲜半岛音乐的使用,防弹与嘻哈文化的关系,防弹疫情期间专辑《BE》中表现的家庭亲密感,《血汗泪》与西方经典文化的关系,《黑天鹅》与现代舞和冷战的关系,都可以升华到对于这些歌曲与音乐视频如何成为美利坚帝国下诗学表达形式的分析。
玛丽·傅盖蒂(Mary Fogarty)和吉娜·阿诺德( Gina Arnold)2021年在《当代音乐评论》(Contemporary Music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你准备好了吗?重新评价泰勒·斯威夫特”(Are You Ready for It? Re-Evaluating Taylor Swift)的文章,开头动情地写道:“泰勒·斯威夫特是那个曾经存在于美国的理念的纪念碑。她让人回想起一个古老的美国梦想……(这是)一个非常古老、非常白的基督教国家。”如果说泰勒的歌勾起的是对传统白人基督教共和国的美利坚的怀旧情绪,那么以防弹为首的K-pop歌曲展现的是事实上是多族群多肤色帝国的美利坚的一种未来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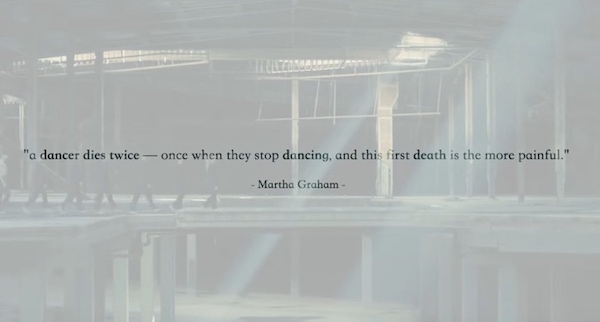
《黑天鹅》艺术电影版一开始对现代舞者玛莎·格拉汉姆话语的引用,按照《读本》主编之一汪育恬(Yutian Wong)的说法,这是对1950年代冷战的回顾。
《读本》第二部分则更多从媒体消费的角度对防弹作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展开讨论,这些文章讨论的议题有对K-pop与平台经济的关系、防弹视频的全球流传、用画作对防弹音乐视频的新的诠释、麦当劳推出的防弹套餐、防弹与黑人文化的关系、网上防弹粉丝关于防弹的讨论与媒体创造形成的数据库、田柾国2022年一次表演延伸的表情包。这些文章弥补了上述两篇文章缺失的一个重要视野:社交媒体平台与网络。尽管两位作者为有关防弹的讨论带来了历史厚重感与批判性深度,但媒体视角的相对缺乏,的确会让人觉得夏威夷草裙舞与防弹的舞蹈完全一样。而社交媒体视角则可以促使人们进一步去思考防弹及K-pop与美国帝国主义下传统服务型经济与表演的区别。或者说,尽管K-pop根植于朝鲜战争后为驻韩美军提供的表演,而从“徐太志与孩子们”开始K-pop产业一直以来对社交媒体和网络与时俱进的运用,让这样的服务经济华丽转身。当然,美国帝国主义视角也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美国主导的平台经济与美国帝国主义统治的新面孔的讨论维度。

2021年麦当劳推出的防弹套餐
《读本》第三部分讨论的是K-pop与社会政治运动的关系,包括防弹粉丝在音乐平台上刷分及背后的社会运动、疫情期间印尼防弹粉丝对印尼国会修订环境与劳工权利保护法案以利于资方的反抗、菲律宾防弹粉丝对菲律宾前总统乐尼(Leni)的支持、土耳其防弹粉丝在一位防弹粉丝女孩遭受父亲冷暴力后自杀而引发的集体游行与示威、防弹歌曲《春日》就韩国2014年沉船事件的隐射,等等。这些文章的特点在于展示了世界不同地区的防弹粉丝如何介入社会公共议题,防弹的歌曲又如何介入韩国社会公众事件。如果说上述两篇文章非常具有批判性地揭示出在拜登接见防弹成员这一表面上的进步包容姿态背后,是美国帝国主义内在结构的自我矛盾,那么这些围绕防弹粉丝介入公共社会运动的讨论也有潜力进一步挖掘批判性和内在张力,而不是停留在对公共与媒体话语的学术语言转化上。
《读本》最后一部分的重点是关于防弹对于防弹粉丝的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的第一篇是由独立作家和学者莎拉·墨菲(Sarah Murphy)撰写的非虚构作品《肌肤之亲日记》(The Skinship Diaries)。文章关于2020年在首尔的一个音乐颁奖典礼上防弹两位成员田柾国和金泰亨做出的一些勾肩搭背举动以及作者对这段视频的反复观看,进而联系自己幼时及早期恋爱经历中由于身体问题而导致得不到足够亲密的关系,却在防弹成员视频中得到了虚拟式的补偿,并且特别也强调了自己更早时候追披头士的经历。类似的文章是第23章《允许欲望》(Permission to Desire),《读本》主编之一拉尼·纽蒂尔(Rani Neutil)以印度裔身份讲述了自己从小在美国的生活经历里缺少正面的亚洲人形象,防弹成员如何满足了这一童年和青少年事情的缺失,帮助她重新认识自我。还有最后一章,《让我们照亮黑夜:防弹少年团与世界终结时废警主义的可能》(Let Us Light Up the Night: BTS and Abolitionist Possibilities at the End of the World),作者乌延西·陈·迈尔(UyenThi Tran Myhre)作为来自越战难民家庭的后裔,也以自传的声音记录了在其工作的明尼苏达州双子城——在疫情初因为弗洛伊德事件而成为废除警察声音中心——如何由于各种压力成为防弹粉丝,并指出防弹现象与废除警察运动具有对未来另类世界展望的同构性。这三篇非学术性的非虚构文章,以第一人称展示了防弹对美国公民的“治疗”作用,从实践意义上呼应了维库尼亚·冈萨雷斯文章的主要论点。这一部分的其他文章涉及防弹对突破父权制想象的意义、成立“防弹学者”网站的实践反思、以防弹专辑为概念进行艺术策展、防弹对穆斯林粉丝的意义等等,都从不同维度表明防弹成员提供的媒体情感劳动的价值和意义。
当两篇批判性极强的文章和一些批判性潜力没有那么充分发挥出来的文章以及自传性和自我代入极强的文章放在一起时,显然很难用评论学术著作的方式来进行评价。相反,我更愿意从美国帝国主义内在矛盾和亚洲种族政治与K-pop偶像的交汇点出发,来考察《读本》在何种程度是以防弹为代表的K-pop在疫情期间为美国观众提供情感治疗效果的元学术性反映,这背后又如何反映出传统公理世界观与学术话语共同体遭遇的危机和面临的转型。当疫情让学者们在家里通过网上教课与工作时(正如《读本》里指出,这其实是一种奢侈),K-pop如何提供了传统学校与学术界共同体之外的另类需求。或者说,当疫情验证了大学教学与学术活动不再需要占有物理空间的时候,包括K-pop在内的社交媒体文化如何弥补了在学校物理空间基础上发展出的共同体与学院生活感的缺失。
这也再次提醒我们,19世纪从德国发展出的现代研究型大学体系及其配套的中小学教育体系在20世纪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全世界想象青少年成长历程的标准化维度,仅仅是一个世纪之内的事,并非自古以来和天经地义。回到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对于天理世界观向公理世界观的转变如何在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形成上得到最显著的表达的讨论,这一论述中相对缺失的一个维度是,作为维护科学话语共同体生产与再生产制度化空间的现代大学如何建立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的中小学教育体系如何跟上(这个问题在讨论张君劢思想时被附带讨论)。也就是说,在欧洲现代性实践及其全球扩张的进程里,德国研究型大学及基础教育体系的建立与传播是思考世界范围内公理世界观建立和普及不可缺失的一环。
如果说科学技术、现代教育体系、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相互作用是构成公理世界观的政治经济制度基础的话,在当代科技基础上发展出的社交媒体文化(K-pop是其中重要一部分,可能会是未来最重要的一部分),又生产出了对公理世界观的否定物。汪晖从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形成角度进行的现代性批判和反思给当代流行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维度是:尽管在媒体研究里20世纪以来流行文化的演变与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里无疑是基本常识,但没有人进一步追问过,20世纪以来的大众媒体文化在何种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科技文明最直接的美学与文化形式?也就是说,在一般文化批判意义上反映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文化(诗歌、小说、古典音乐、歌剧等)等都是前资本主义文化在资本主义科技与经济条件下的现代转化,而非资本主义科技直接生产出来的美学与文化形式。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的过去一切革命如何使资产阶级国家以最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说过去一切技术革命最终使资产阶级文化通过社交媒体大众文化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与此同时,作为欧洲中世纪行会组织的大学,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后选择的现代性模式道路是将其废除(大革命关闭了巴黎大学,直到1870年代普法战争后才真正重建,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巴黎政治学院社会学家克里斯汀·姆赛琳[Christine Musselin]的经典著作《法国大学的长征》[La longue marche des universités françaises]),作为回应,德国走了将中世纪教授神学的大学转化为进行现代科学研究的大学的道路。这说明最终获胜的德国模式并非注定是现代性的必然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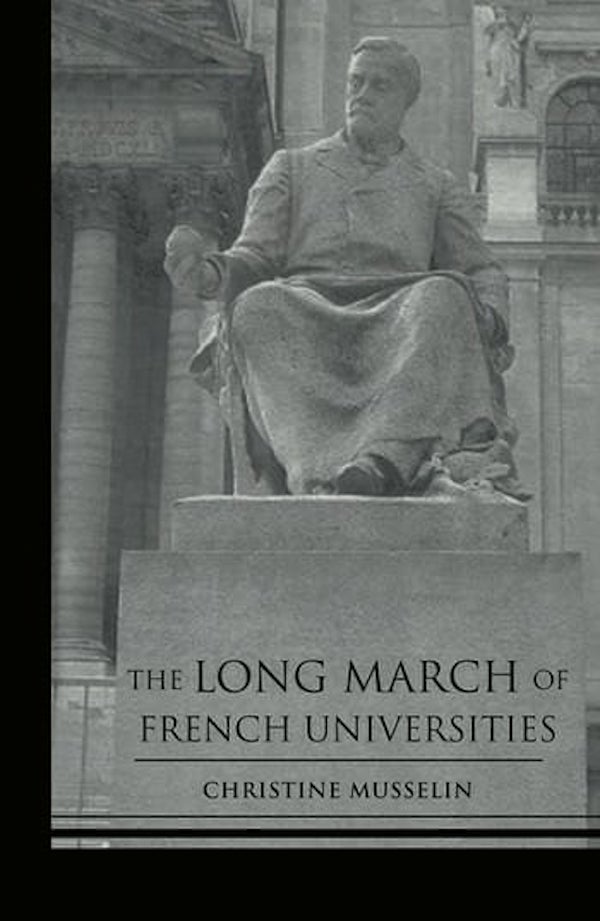
《法国大学的长征》2001年英语版,劳特里奇出版社
因此,当进入娱乐公司当练习生成为无数韩国青少年上大学的一个替代品时(相应的评价标准是进入四大娱乐公司的价值等同于进入SKY三所韩国精英大学),这并非单单是朝鲜半岛南部的一个独特现象,而是德国大学模式及教育体系在大众传媒文化面前逐渐被替代的一次预演。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李昭仑(So Yoon Lee)目前正在进行的韩国以输送练习生为目的的学校机构的田野研究的未来潜在价值,可能可以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类比。今天没有人会将恩格斯的作品仅仅当作对英格兰的一项“区域研究”来看待,而是将其作为理解第一次工业革命下现代文明展开及劳动异化的一项麻雀解剖式研究,因为恩格斯在英格兰调查的结果预示着欧洲大陆及欧洲以外地区都要经历的一个现代化过程和与之相伴的痛苦与道德伦理危机。同样的,如果我们只用区域研究思维来看李昭仑研究的意义也会是片面的,这项在朝鲜半岛南部展开的田野背后是与公理世界观和科学话语共同体转型紧密相关的现代教育体系如何让位于大众文化的问题,或者说大众娱乐公司及其预备学校如何取代现代大学及中小学来作为青少年成长的组织化机构,以及扎根于当代科技的流行音乐舞蹈训练如何成为数理化训练之外的另类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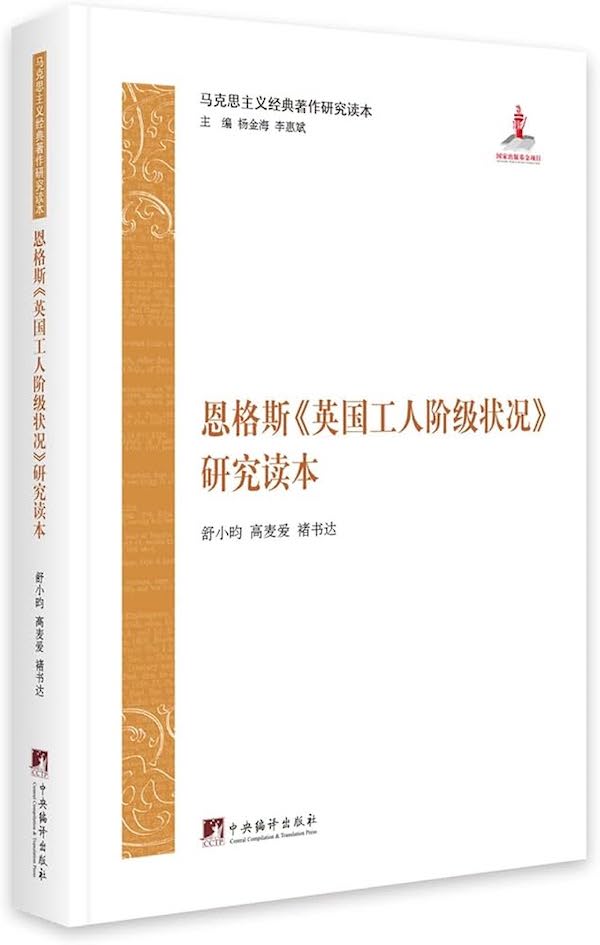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K-pop兴起的本质并不是韩国民族主义者所说的韩国的兴起,也不是亚洲中心论学者强调的亚洲的崛起,K-pop兴起的本质是当代大众文化本身的兴起:流行文化从一种民众茶余饭后的消遣上升到一种对个人发展与价值观追求有极大影响的美学语法与价值体系,而后者本身是传统学校教育的任务,只是这一过程刚好从韩国起步,正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英国起步一样。因此,《读本》既代表着作为世界学术中心的美国对K-pop兴起的批判性回应,更记录着美国大学里公理世界观及传统学术共同体在大众文化塑造下的一次转型尝试。
伴随着防弹全球热,英语学术界对于防弹的讨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我一直好奇的一个问题是,韩国娱乐公司的产业界人士是否会关注这些讨论?比如《读本》是否会被防弹所属的HYBE公司作为圣经一样阅读?或者说,学术界是否能影响产业界?尽管我无法做猜测,但正如《读本》里第6章作者Dal Yong Jin讨论K-pop与社交媒体平台发展的演变所暗示的,相比于对K-pop的人文学术讨论,韩国娱乐公司的制作人们可能更需要以AI为代表的科技发展。正如上文所说,当代大众文化本质是科技文明自己的美学和文化形式。如果说公元前5世纪末关于酒神的悲剧《酒神的伴侣》代表的是纪念碑式的剧院及其传播(背后是古希腊罗马一项重要制造技术)对古希腊民众听觉视觉体验的彻底重构,那么防弹2019年的作品《狄奥尼索斯》揭示的是,K-pop音乐带来的大众非理性狂欢体验取决于高度理性算法运作下的社交媒体网络平台。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可以重读马克思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结尾对狄奥尼索斯形象的引用:
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郑锴宸同学通读全文文稿,对文中有关《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讨论提供了修改意见,在此特别感谢。)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